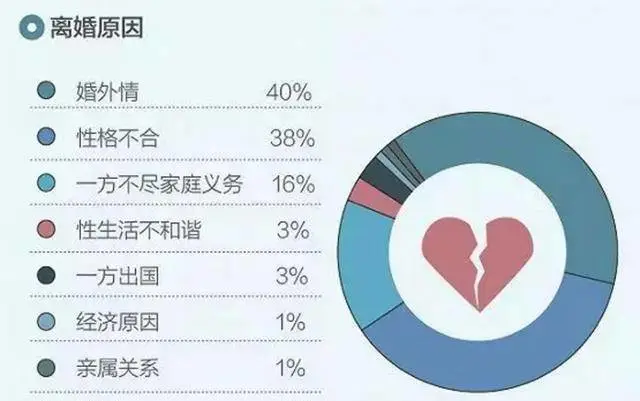替别人讲故事是很难的,特别是替女人讲心事。中国自古都有大文人借着闺怨抒发不满的传统,无论是诗以明志或诗以表忠,女人心思与男人命运在古典文学中纠缠在一起,是比喻变化,也是心口不一。心事当然不存在什么性别差异,但“女人心海底针”不知从何时起口口相传,“中年妇女”有时也是一个骂人的词了——当她被追求时,那些事都当作神秘而可爱的存在;当她被厌恶时,那些事则成了她病态和不值得认真对待的根源。人到中年,就被视为完全成熟的动物,七情六欲似乎都该收敛起来。男人要稳重,女人要端庄,这是古典的美学与礼教,女人的心事因此是成了多余物,只要稍微显露出来,便成了他人腹诽和嚼舌的把柄。张楚新写了一篇小说,名为《中年妇女恋爱史》,说的就是这些被恶意包裹、遮蔽的事,以及它们的前因后果、一饮一啄。
可能现在没有人比张楚更适合来讲这些故事了。读过他的《忆秦娥》《樱桃记》《略知她一二》和《良宵》等篇目,便知他对纤细心思和刹那感觉的敏锐把握。如果女人心真如海底针般不可捉摸,张楚的笔触当有足够的磁力去收集、整理和重新讲述那些女人的故事。张楚对“她们”关注已久,也已在心中反复考虑过,写作一组女人的心事和故事,是水到渠成的。更何况,张楚在写女性角色时一向温柔诚恳,当今文坛少见这样的行文语气,似强者的私语,坚硬却又温柔,十七岁少年的热情和保护欲弥漫在纸上。尽管张楚有意识地降噪作者的声音,从西方现代短篇好手中学到了精细克制的第三人称叙事技巧,但叙述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事,它会暴露叙述者的内心节奏,甚至私人的情绪。张楚在讲她们的故事时,越是冷静就越显关切呵护之心,丝毫不插入对她们的心思的过度解读和定义——张楚是爱她们的。
这成就了《中年妇女恋爱史》。受屈辱、受惩罚的女性形象不见了,近似疯癫、困于他者的“恋爱中的女人”也消失了。小说中的茉莉、甜甜、老甘和小五是再普通不过的女人,她们没有军干背景,与热闹的官商名利场毫无瓜葛,她们在婚姻中颠沛流离,尝过不同味道的身体,在期待中学会妥协和将就,直至最后,男男女女的二人世界不再浪漫,她们从此只能咀嚼生活的甘苦。小说的主题简单而明确,要替那些年风情万种的她们讲故事,风情万种怎么就变成了甘苦二味?这便不能不从头讲起,从历史上反顾命运巨变的关口了。
评论家常觉得张楚长于抒情,能在抒情的声音中讲诉人间百态,从而避免了与现实正面对抗的紧张与焦虑。是呀,抒情的声音控制着他对不公平与虚情假意的控诉,细微感情也能传达出人间大义。抒情未必就是对现实的压抑和不见,情感的迂回和舒展之中有着历史事件真实的律动。只是,抒情的风格往往都意味着思想的自制,意味着文字的符码中有着不可广而告之的“暗号”,懂的人能共情,能读到背后的关怀或愤怒;不懂的人就一跃而过,以为不过如此。在《中年妇女恋爱史》中,张楚似也忍不住了,想把抒情的“暗号”送到了阅读者的眼前。书中主角的恋爱故事要从1992年讲起,每五六年间一场变故,暗暗呼应着时代洪流忽而泛起的漩涡。小说各节标题都是年份数字,1992、1997、2003、2008、2013,明面上的“恋爱史”被这些年份背后的“大事”破题,恋爱史中的茉莉和她闺蜜们未曾从“改革开放”和“新世纪”的洪流中孑然独立。细读之,与茉莉交集关联的男人们在出场时都带着时代的“味道”,茉莉和他们谈恋爱、过日子的方式无一不在时代的氛围中。
这可能是截止目前张楚最为“怀旧”的小说了吧,小说中的服饰、音乐、气味和观念,都十分具体,组成了一个召唤记忆的符合序列,既让虚构的恋爱故事变得丰富,又使读过的人在脑海中自觉填补画面。抒情与历史相逢,便有了“昨日重现”的文本效果。张楚用心地在故事中点明物件名称、歌曲唱词、新闻线索(小兔情感挽回老师 微信:ke2004578),不是简单地怀念旧物,在词与物的过往浮影中他塑造了人物的变化、死亡和退场。小说第二节死亡的甜甜和在结尾时“退场”的小五,更像是替茉莉受罪一般,这些女人的命运看似千差万别,其实也不过是在悲惨与活着二者之间被命运拨弄,她们选择什么样的男人,就几乎等于选择了怎样的人生。
张楚在叙事过程中精心插下的怀旧片段,是她们人生的镜像碎片。当时当事的浪漫与漫不经心,导致了今时今日的破败和一地鸡毛,茉莉和闺蜜们的恋爱经历在被张楚对照时代密码簿重新编辑后,终于显出了所谓“情史”背后的草蛇灰线——这些生于改革开放时代的少女以为自己能选择所爱的人,却没想到庞然无形的历史会在爱情选择中左右自己。小说里作为“怀旧”的服饰、音乐、气味无一不是时代的“症候”,当男人们不再成为茉莉需要依附、衬托的他者时,这些时代的“症候物”实际上是茉莉情感选择的真正对象。随着少女成熟,改革开放发展为“新时代”,人近中年的茉莉已不再迷恋时代新潮,她与彼时的新新人类、网络媒体无关,甚至倦怠于新的感情,交往活动都退回到麻将桌上。作为症候的时代物此时反而退出茉莉“欲望的三角”,桀骜、油滑又猛烈的青年身体重新闯入茉莉的中年生活,小说以一场牵连闺蜜的骗局收尾。2013年,历史虽未完待续,茉莉的恋爱恐怕要以此为终点了。据张楚说,他原本打算继续写一节,让老甘在休养院里推着坐轮椅的茉莉,但他还是觉得小说到此为止更好。的确,作者不必写恋爱史的终章,没必要残忍扒开茉莉那枯死的心,张楚是爱她们的。
“欲望的三角”是法国学者勒内·吉拉尔的话,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替罪羊》等著作中,他批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把人的自主性夸大其实,大多数人哪里有那样坚硬又有力的内核。他认为,人直接形成欲望并付诸行动是不可能的,欲望存在于模仿的三角中——人要通过模仿中介才能完成欲望。吉拉尔反对浪漫主义对康德哲学的过度阐释,他把《唐吉坷德》和《包法利夫人》放在一起看,道出了小说中“浪漫的谎言”不过是掩盖欲望的中介,人无法依仗自己“产生”欲望,而只能通过模仿一个或敌或楷模的第三者触及欲望。对吉拉尔来说,好的小说家就是要明确揭示出“中介”的作用,而平庸的作品不过是在掩盖它。《中年妇女恋爱史》在这个意义上看是难得的好小说,它细细回忆出浪漫恋情的点点滴滴,既是一种时代的怀旧,也是对爱欲“中介”的抒情化展示。作为中介的时代症候在她们的恋爱史慢慢显明,对错、优劣、崇高与卑下等等时代观念假借服饰、音乐和气味构筑了茉莉的爱欲,作家由此揭露“浪漫的谎言”,抵达“小说的真实”。《中年妇女恋爱史》中的女人,并非遇人不淑,但却缺少“良媒”,她们每一次恋爱都模仿、承受着爱欲中介的错误。小说在明线上代替茉莉说话,倾述茉莉从初恋到首婚,从背叛到被背叛的恋爱故事,一任任的情人填补着茉莉不同人生阶段对男人、人生的想象。但张楚在暗地里怜惜和悲痛的,是茉莉、甜甜、老甘和小五每一次恋爱,都在福楼拜笔下包法利夫人和阿尔努夫人的影子中,她们模仿她们想变成的那个人,从头到脚地去模仿她们以为真正爱情应该有的样子,却一误终身,在历史的每一个拐点都做出了对自己最坏的选择。
《中年妇女恋爱史》在抒情与写史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点,满是复杂意义的年份标题与那些看似顾左右而言他的大事记组成各节的首尾,她们的故事附上了时间的刻度,男男女女的聚散离合有了隐喻意味。由此看来,张楚的抒情从来不缺深度和历史感,只是在如今社会气氛中,抒情之笔往往被人们忽视,以为此类笔法只能在爱恨之间试探人心人性,以为它承受不住生命哲学、政治理论和经济法则的宏大论题。知否,知否?情感哪里是无中生有的产物?一直以来用心深入揭露人性的张楚,肯定还相信着“情不知所起”的浪漫谎言,但他也没有忘记“小说的真实”,张楚在男男女女的红尘故事中追问爱欲所依附的中介物。

尽管每节附录的大事记有时显得过于直白,有时又显得乖张了一些,但张楚站定了写作的平衡点,在这个短篇小说中从未失去叙述的分寸感。所谓“叙述的分寸感”,要既不流于浪漫的谎言,不能错把恋爱当作女人们生命的全部,又要不以史论冒犯读者,不借题发挥把叙述上升为论理。在书写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故事时,这种分寸感极为重要,不入玄理,不走极端,不借命案、悬疑或鬼魅来讲述新时代中国人的荒诞与悲苦,这是当代写作的大难之事——被时下中国当代文学史记录新时期小说,多数以此留下浓墨重彩,似乎寻常琐碎的爱情故事与当代史无缘了一般。在它们之间,张楚写小说时的“抒情力”与“分寸感”就显得很难得了。
若无意于解码文本与历史的互动关联,《中年妇女恋爱史》也别有一番可供讨论的余味。张楚爱护笔下的人物,极少议论他们所选择的生活形态,哪怕这注定是悲剧,他都能以同情同理的心态去把故事讲下去。替茉莉她们讲恋爱史,同情于她们的遭遇,这个写作的立场搁置了道德的迷信。小说因涉及恋爱史,必然会展示关于恋爱的观念和禁忌。学者杨联芬有一篇有趣的文章,在《恋爱之发生与现代文学观念变迁》一文中,她借助“恋爱”这一关键词,考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人对男女之情的看法。恋爱是作为新词从日本引入现代中国,在本土化的早期,“恋爱”被旧的性道德观念视为不循旧制的男女之情,甚至有乱性之义,而后“恋爱”与五四“自由”、“独立”等观念相连,语义之间带有青年人独立自主的意思。彼时还有激进的观点引发一波波讨论,如张竞生在1925年提出个人拥有认定情感关系的全部权力,多夫多妻的情人关系也当被社会承认。即便如此,真实生活中五四一代的“自由恋爱”,也未曾独立于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张楚深知,笔下的女性与五四之子处境类同,看似“独立”“自由”“开放”的时代风气,并没有给予她们足够的尊重,女人们的爱欲和恋爱选择并不独立于历史发展,她们表达爱欲的权力都受制于主流的道德观点。甚至,这些遭遇婚姻不幸的当代人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恋爱”问题只能在茶余饭后被闲说,没有人会觉得茉莉的婚恋不幸与改革开放有任何关系。小说中,茉莉的初恋萌动,都是在“商品粮”、“农业粮”这类“门当户对”的观念中纠结。十一年后她和高宝宝再相遇,婚姻的城乡二分观念已经被改革开放晃动瓦解,可他们哪里能重头来过?茉莉并非孑然一身,她被现任“男友”撞见和高宝宝的死灰复燃,一切尴尬与不堪倒是在她身上不断重复。在宣称“自由恋爱”的改革时代,茉莉的恋爱似乎仍然是不足为道的“丑事”,那个宣称“稳定”、“优生”和“健康”的婚姻观念仍然笼罩在茉莉和她闺蜜们的爱欲之上。张楚的小说无意于否定婚姻制度,但观照了婚姻不幸者的恋爱问题,这是当代史的阴暗一角,许久没有人触及了。中年妇女的爱欲应该怎样在一夫一妻婚姻家庭范畴之外被社会认识和理解呢?“中年妇女恋爱史”一说,多少有些重新思考那套婚姻爱情观念对个人的意味,即,在改革开放史中重新定义“恋爱”何谓。
小说中茉莉的最后一次恋爱,一开始并不是你情我愿的。茉莉的身体已步入中年,她对浪漫爱情也不再有那么多奢想,一次次出人意料的出轨和背叛让她无力。此时牌桌上出现的青年人,似是茉莉的新朋友,却对她不怀好意。蔡伟像捕猎的豹子,在夜晚主动出击,他年轻、强壮,让茉莉“难以抗拒”。此时的茉莉依然还能闻到爱欲的味道:
“其实也觉得荒唐中年男人谈恋爱的心里,她自己倒好,独身,孩子也懂事了,可他呢,也没听说家里如何如何,跟自己这么着,无非是图个新鲜罢了。男人是如何的德行,她一清二楚。久了,够了,腻烦了,拔腿就走。知道是这样的理儿,躺在他肉上,闻着毛孔里松脂的味道,还是难免有些沉醉。她晓得,这种事情,女人总是吃亏的,可是,倒也无所谓了。”
就算是对男人一清二楚的茉莉,也难免有些沉醉,而只要一个恍惚,命运就又一次不留情面地击碎茉莉对美好爱情是生活的奢想。蔡伟在一次有着“私奔”意义的旅游途中拿着茉莉的储蓄逃走,茉莉有苦无处述说,还不知这个青年人的连环骗有多恐怖。2013年,茉莉已经不再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和其中风一样的男子,学老甘退回了半封闭的私人生活。她的恋爱故事似乎无所谓时代意义了,但剥离了那些作为症候的服饰、音乐和气味,茉莉的苦与难又有谁来述说呢?在时代潮流中她们身不由己,在红尘滚滚中她们有苦难言。
读《中年妇女恋爱史》,最终留在心头的还是张楚运笔时的温柔暖意。这些中年妇女的故事如此残酷,他还能守持叙述的平衡,不冒昧、不闪烁,不尝试以时下的道德律令强作解释,留下了“恋爱史”中值得回味和深思的瞬间。这个小说,把女人的心事与中国改革开放史做对读,是写给作者同时代人的情感史。而张楚这个说故事的人,好似本雅明所赞誉的来往行者,他既讲别人的故事,又改造了这些故事以影响正在听的人,张楚的小说诞生于红尘与时代之间,是对切己问题的关怀和深情。好在他写小说时有分寸,拉开了距离看红尘,对同代人身上背负的幽暗隐晦之物有着极敏锐的知觉,这时候,说故事的人也就成了燃灯者,成了阿甘本所期待的同代人。讲故事的燃灯者或激烈地献身,与幽暗隐晦之物对抗;或智慧地回旋,在他处照见情理的余脉;或如张楚这样,藏一盒火柴在身上,若有故人来便取火照明,火光中她们风情万种,把血污留在背后的阴影中。
多亏了和她们同时代的张楚,还在坚持小说创作,还在相信文字之情能宽慰性灵。抒情对当代作家来说可能是个烫手的山芋——如果对历史与现实中的幽暗隐晦有所察觉,如果还尝试冲破思维桎梏去形成复杂思考,就不免会在写作时出现雄浑的、激烈的、悲怆的、滑稽的甚或怪诞的文体。对于这类严肃的创作来说,抒情意味着什么?张楚的尝试,意味着抒情化处理历史症候是可能的。
多亏了《中年妇女恋爱史》,不然就算她们有千种风情和万般无奈,更与何人说?